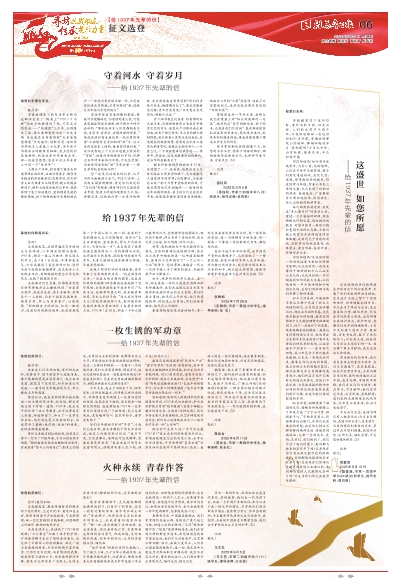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8月21日
一枚生锈的军功章
——给1937年先辈的信
尊敬的曾祖父:
展信安!
此刻是2025年的初秋,窗外阳光正好,街巷安宁。孩子的笑声从远处传来,楼下餐铺的蒸笼正冒着热气。我坐在书桌前,提笔写下这封信,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因为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早已超出当年的想象。
前些日子,我在老家的樟木箱底翻出一枚生锈的军功章。祖母说,那是曾祖父留下的唯一遗物。1937年,他是北平郊外的一名小学教员,本可以带着家人南逃,却选择留下,加入了一支学生游击队。他们用毛笔书写标语的手,后来学会了握枪;他们教《论语》的嗓音,最终在战壕里喊哑。
曾祖父没能活到抗战胜利,档案里只留下一行字:“1938年春,于房山阻击战中殉国。”那枚勋章是他战友辗转送回家的,背面刻着“誓与山河共存亡”。勋章上的锈迹,是曾祖父未尽的话语。我摩挲着这七个字,突然想起去年参观抗战纪念馆时,见过一支锈蚀的钢笔——它属于一位战地记者,笔杆上还留着弹痕。解说员说,这位记者牺牲前最后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今夜星光灿烂》。您是否也曾在硝烟间隙抬头,相信后世能看见完整的星空?
今年七月,我去卢沟桥走了走。88年过去,石狮依然矗立,但弹痕已被时光抚平。导游指着宛平城墙上一处修补过的砖块说,这里原是个炮洞,现在嵌着一株野生的枸杞。我忽然想起1937年一位守军日记里的片段:“子夜轮岗,见月光照残垣,竟有蟋蟀鸣叫。想家中幼子,该学会走路了。”
你们当年拼死守护的“寻常”,于我们已成日常。桥头卖糖葫芦的大爷告诉我,他家三代都住在这附近。“我爷爷说,打完仗那天,他蹲在河边洗绑带,发现水里竟有鱼苗。”现在永定河两岸全是遛弯的人,傍晚常有老人拉二胡,调子是《松花江上》。
最近总在新闻里看到“新质生产力”“量子计算机”这些词。若您知晓,当年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的同胞,如今正用卫星导航种粮、用5G技术救灾,该有多欣慰?您种的树,现在已长成森林。去年贵州“天眼”射电望远镜接收到137亿光年外的信号时,有位老工程师哽咽道:“这和当年摸黑修滇缅公路是同一双手。”
您知道吗?您那代人的精神早化作基因里的密码。2020年武汉抗疫时,护士在防护服后背写“精忠报国”;扶贫干部翻山越岭的背包里,总揣着《论持久战》。我们不再需要以身躯堵枪眼,但芯片研发的实验室里,照样有人连续熬夜攻关——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上甘岭”?
偶尔会听见有人问:“为什么总提1937年?”我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看墙面裂缝里生出的白色小花;去重庆防空洞遗址,听导游讲解“雾季公演”时演员如何在轰炸中坚持演出《屈原》。最动人的是一张泛黄剧照:观众戴着钢盔,舞台灯光却亮如白昼。历史不应被遗忘,记得比遗忘更有力。
搁笔前,我又看了看那枚军功章。锈迹之下,隐约能辨出图案的轮廓。88年足够让青铜氧化,却从未让誓言褪色。此刻夕阳西沉,广场上响起《我的祖国》的旋律。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跑过,他们衣领太干净,还没见过真正的血与火。但当我听见他们争论将来要当科学家还是军人时,忽然明白了传承的意义——你们披荆斩棘的路,我们接着走下去。
此致敬礼!
蒋宜含
2025年8月10日
(蒋宜含,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指导老师:余永红)
展信安!
此刻是2025年的初秋,窗外阳光正好,街巷安宁。孩子的笑声从远处传来,楼下餐铺的蒸笼正冒着热气。我坐在书桌前,提笔写下这封信,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因为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早已超出当年的想象。
前些日子,我在老家的樟木箱底翻出一枚生锈的军功章。祖母说,那是曾祖父留下的唯一遗物。1937年,他是北平郊外的一名小学教员,本可以带着家人南逃,却选择留下,加入了一支学生游击队。他们用毛笔书写标语的手,后来学会了握枪;他们教《论语》的嗓音,最终在战壕里喊哑。
曾祖父没能活到抗战胜利,档案里只留下一行字:“1938年春,于房山阻击战中殉国。”那枚勋章是他战友辗转送回家的,背面刻着“誓与山河共存亡”。勋章上的锈迹,是曾祖父未尽的话语。我摩挲着这七个字,突然想起去年参观抗战纪念馆时,见过一支锈蚀的钢笔——它属于一位战地记者,笔杆上还留着弹痕。解说员说,这位记者牺牲前最后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今夜星光灿烂》。您是否也曾在硝烟间隙抬头,相信后世能看见完整的星空?
今年七月,我去卢沟桥走了走。88年过去,石狮依然矗立,但弹痕已被时光抚平。导游指着宛平城墙上一处修补过的砖块说,这里原是个炮洞,现在嵌着一株野生的枸杞。我忽然想起1937年一位守军日记里的片段:“子夜轮岗,见月光照残垣,竟有蟋蟀鸣叫。想家中幼子,该学会走路了。”
你们当年拼死守护的“寻常”,于我们已成日常。桥头卖糖葫芦的大爷告诉我,他家三代都住在这附近。“我爷爷说,打完仗那天,他蹲在河边洗绑带,发现水里竟有鱼苗。”现在永定河两岸全是遛弯的人,傍晚常有老人拉二胡,调子是《松花江上》。
最近总在新闻里看到“新质生产力”“量子计算机”这些词。若您知晓,当年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的同胞,如今正用卫星导航种粮、用5G技术救灾,该有多欣慰?您种的树,现在已长成森林。去年贵州“天眼”射电望远镜接收到137亿光年外的信号时,有位老工程师哽咽道:“这和当年摸黑修滇缅公路是同一双手。”
您知道吗?您那代人的精神早化作基因里的密码。2020年武汉抗疫时,护士在防护服后背写“精忠报国”;扶贫干部翻山越岭的背包里,总揣着《论持久战》。我们不再需要以身躯堵枪眼,但芯片研发的实验室里,照样有人连续熬夜攻关——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上甘岭”?
偶尔会听见有人问:“为什么总提1937年?”我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看墙面裂缝里生出的白色小花;去重庆防空洞遗址,听导游讲解“雾季公演”时演员如何在轰炸中坚持演出《屈原》。最动人的是一张泛黄剧照:观众戴着钢盔,舞台灯光却亮如白昼。历史不应被遗忘,记得比遗忘更有力。
搁笔前,我又看了看那枚军功章。锈迹之下,隐约能辨出图案的轮廓。88年足够让青铜氧化,却从未让誓言褪色。此刻夕阳西沉,广场上响起《我的祖国》的旋律。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跑过,他们衣领太干净,还没见过真正的血与火。但当我听见他们争论将来要当科学家还是军人时,忽然明白了传承的意义——你们披荆斩棘的路,我们接着走下去。
此致敬礼!
蒋宜含
2025年8月10日
(蒋宜含,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指导老师:余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