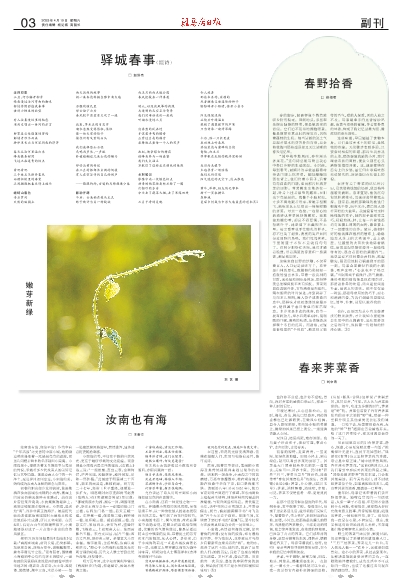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4月19日
春来荠菜香
□ 刘中海
也许你不喜爱,也许你不爱吃,然而,我对荠菜的感情由来已久,那是一种儿时的记忆。
乍暖还寒时,人心已然松动。这时,梅花、杏花、桃花已然盛开,河边的垂柳也已吐露鹅黄,在微风中轻舞。最令人感叹的是,菜市场小贩的菜摊上,嫩绿的荠菜已摆上摊位,一缕缕清香飘入心间。
双休日,艳阳高照,难得温暖。我与妻子带着孩子,提着竹篮,拿着小铲,走向原野,走进春天。
初春的原野,麦苗青青,一望无际,如绿色的地毯。田间小径上,刚有绿色,就可以看到荠菜的身影了。荠菜是大自然奉献给春天的第一道美食,美味可口、营养丰富。民间有“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谚语,还流传着“春食荠菜赛仙丹”的说法。崔禹锡《食经》载:荠菜,补心脾。《陆川本草》:荠菜,消肿解毒,治疮疖,赤眼。可见,荠菜不仅是佳肴一碟,更是灵药一方。
在那个还没有解决温饱的年代,每到春季,家中就断了粮。每每那时,母亲干过家务活儿后,就带领我们兄妹几个,提着篮子,带上铁铲,来到附近的山坡、田埂、小河边,挖那些最先露头的野菜,当然挖的荠菜最多。当你走近的时候,就会惊喜地发现,在枯黄的野草里,已掺杂了青青的荠菜。它们那单薄的身躯,正冒着微寒的东风,拥挤着、嬉闹着赶春来了。母亲带着我们,挖呀,挖呀!母亲弯着背寻找野菜的身影,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如故。
荠菜,生于田野,耐寒力强,田边、地头、蒿草丛,都能顽强生长,一点阳光、一滴水分、一缕春风就可以生存。我一直觉得它有着朴实倔强的品格。《诗经·邶风·谷风》这样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可见,古人认为荠菜是甜的。如今,吃过太多甜的时代,荠菜是“野”的。荠菜包成饺子后有着荠菜独有的近乎大地的“野”味,那是一种泾渭分明且其他菜类无法匹及的味道。一口咬下去,味蕾瞬间被充盈,大地的“鲜”“野”随即在舌尖铺散开来。吃了这口荠菜饺子,那这可真是奢侈的一天了。
坐在城里自家的阳台择荠菜,静心,惬意,心里反复默念着一句话:“挑根择叶无虚日,直到开花如雪时。”陆游在《食荠》诗文里将荠菜视为珍蔬,夸它是中原正味。“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首《鹧鸪天》,让我们看到辛弃疾对荠菜的喜爱之情。“时绕麦田求野荠”的苏东坡,只会做荠菜羹汤。而今天的我们,时不时就包荠菜饺子吃,如果再配些肉末儿,混合着荠菜的清香,那真是一口鲜呀。
童年时,母亲经常带着我们去田野挖荠菜。她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年轻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挺住,要珍惜大好时光做有意义的事,青春短暂易逝,就像这荠菜,一转眼就开花,老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不曾忘记。现在,我又把这句话讲给我的儿孙听,不知道他们能否理解老人家的心情。
野生的荠菜气味清新、鲜美甘甜,但如果错过了采摘时间就很难入口。“三月三挖荠菜,荠菜花儿一片白,有人挖无人栽……”在乡下,这歌谣妇孺皆知。这小小的荠菜,从过去到现在,从解决温饱到备受追捧的美食,一直默默陪伴着我们,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
也许你不喜爱,也许你不爱吃,然而,我对荠菜的感情由来已久,那是一种儿时的记忆。
乍暖还寒时,人心已然松动。这时,梅花、杏花、桃花已然盛开,河边的垂柳也已吐露鹅黄,在微风中轻舞。最令人感叹的是,菜市场小贩的菜摊上,嫩绿的荠菜已摆上摊位,一缕缕清香飘入心间。
双休日,艳阳高照,难得温暖。我与妻子带着孩子,提着竹篮,拿着小铲,走向原野,走进春天。
初春的原野,麦苗青青,一望无际,如绿色的地毯。田间小径上,刚有绿色,就可以看到荠菜的身影了。荠菜是大自然奉献给春天的第一道美食,美味可口、营养丰富。民间有“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谚语,还流传着“春食荠菜赛仙丹”的说法。崔禹锡《食经》载:荠菜,补心脾。《陆川本草》:荠菜,消肿解毒,治疮疖,赤眼。可见,荠菜不仅是佳肴一碟,更是灵药一方。
在那个还没有解决温饱的年代,每到春季,家中就断了粮。每每那时,母亲干过家务活儿后,就带领我们兄妹几个,提着篮子,带上铁铲,来到附近的山坡、田埂、小河边,挖那些最先露头的野菜,当然挖的荠菜最多。当你走近的时候,就会惊喜地发现,在枯黄的野草里,已掺杂了青青的荠菜。它们那单薄的身躯,正冒着微寒的东风,拥挤着、嬉闹着赶春来了。母亲带着我们,挖呀,挖呀!母亲弯着背寻找野菜的身影,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如故。
荠菜,生于田野,耐寒力强,田边、地头、蒿草丛,都能顽强生长,一点阳光、一滴水分、一缕春风就可以生存。我一直觉得它有着朴实倔强的品格。《诗经·邶风·谷风》这样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可见,古人认为荠菜是甜的。如今,吃过太多甜的时代,荠菜是“野”的。荠菜包成饺子后有着荠菜独有的近乎大地的“野”味,那是一种泾渭分明且其他菜类无法匹及的味道。一口咬下去,味蕾瞬间被充盈,大地的“鲜”“野”随即在舌尖铺散开来。吃了这口荠菜饺子,那这可真是奢侈的一天了。
坐在城里自家的阳台择荠菜,静心,惬意,心里反复默念着一句话:“挑根择叶无虚日,直到开花如雪时。”陆游在《食荠》诗文里将荠菜视为珍蔬,夸它是中原正味。“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首《鹧鸪天》,让我们看到辛弃疾对荠菜的喜爱之情。“时绕麦田求野荠”的苏东坡,只会做荠菜羹汤。而今天的我们,时不时就包荠菜饺子吃,如果再配些肉末儿,混合着荠菜的清香,那真是一口鲜呀。
童年时,母亲经常带着我们去田野挖荠菜。她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年轻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挺住,要珍惜大好时光做有意义的事,青春短暂易逝,就像这荠菜,一转眼就开花,老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不曾忘记。现在,我又把这句话讲给我的儿孙听,不知道他们能否理解老人家的心情。
野生的荠菜气味清新、鲜美甘甜,但如果错过了采摘时间就很难入口。“三月三挖荠菜,荠菜花儿一片白,有人挖无人栽……”在乡下,这歌谣妇孺皆知。这小小的荠菜,从过去到现在,从解决温饱到备受追捧的美食,一直默默陪伴着我们,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