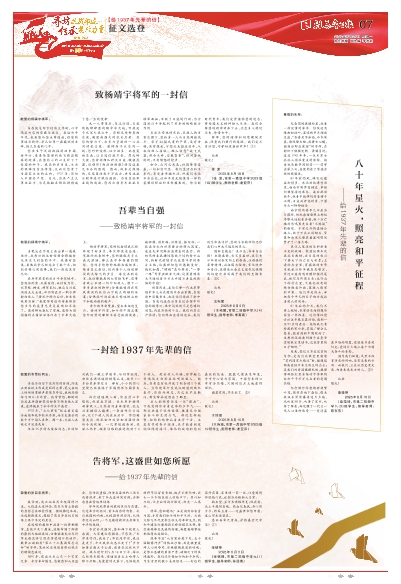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8月25日
八十年星火,照亮和平征程
——给1937年先辈的信
尊敬的先辈:
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放着一封泛黄的家书。信纸边角蜷曲如枯叶,墨迹被岁月洇成淡蓝,“吾妻见字如面,今冬寒甚,前线棉衣缺,然将士心暖,因身后即是家国”的字样,在射灯下微微发颤。讲解员说,这是1943年冬,一位川军士兵托人捎往重庆的家信。他再也没能等到回信——信寄出第三日,他便倒在了常德会战的战壕里。
80年前的风,确实比现在冷得多。东北的林海雪原里,杨靖宇将军靠树皮、草根和棉絮撑过寒冬。最后那场战斗,他身中数弹仍倚着树干不倒,日寇剖开他的胃,才懂什么叫铮铮铁骨。
南京的街巷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但纪念馆墙壁上那组浮雕永远刻着真相,数十万亡魂的悲鸣里夹杂着“不能退”的嘶吼。千里之外的滇缅公路上,数十万民工用锄头、箩筐和血肉之躯在悬崖峭壁间劈开了一条生路。
更让人落泪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战场。教授把课本改成抗日教材,在日寇的刺刀下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海的弄堂里,穿旗袍的女学生把抗日传单藏在发髻里,穿过日寇岗哨时腰杆挺得笔直,把信息传递出去;太行山下的村庄里,大娘把仅有的粮食做成炒面,塞进八路军的口袋。他们不是战士,却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当成抗击敌人的战场。
8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上战场,但有些东西得像传家宝一样捧着。还记得以前去社区开展志愿活动,遇到一位90岁的老兵。他给我们看珍藏的军功章,笑道:“那会儿想着,能看到新中国就好了。没想到还能看到孩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读书,比我梦里的日子都好。”
原来,铭记从不是沉重的负担,是我们在教室里朗读“苟利国家生死以”时,能想起那些在狱中舍生取义的志士;是我们对着国旗敬礼时,能懂得那抹红里有杨靖宇将军的血和千千万万无名者的爱国热情。
纪念馆外的老槐树枝繁叶茂,根须在地下盘结,像无数双手紧紧攥着这片土地。风吹过80年,吹黄了家书,吹锈了弹壳,却吹醒了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热爱——爱清晨菜市场的喧嚣,爱深夜书房的灯光,爱这片土地上每个为明天奋斗的身影。
因为我们知道,风里不仅有历史的回响,还有未来的方向。而我们,正是从历史里走来、向着未来走去的人。
此致敬礼!
柴靖坤
2025年8月10日
(柴靖坤,市第二初级中学八(9)班学生,指导老师:陈东伟)
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放着一封泛黄的家书。信纸边角蜷曲如枯叶,墨迹被岁月洇成淡蓝,“吾妻见字如面,今冬寒甚,前线棉衣缺,然将士心暖,因身后即是家国”的字样,在射灯下微微发颤。讲解员说,这是1943年冬,一位川军士兵托人捎往重庆的家信。他再也没能等到回信——信寄出第三日,他便倒在了常德会战的战壕里。
80年前的风,确实比现在冷得多。东北的林海雪原里,杨靖宇将军靠树皮、草根和棉絮撑过寒冬。最后那场战斗,他身中数弹仍倚着树干不倒,日寇剖开他的胃,才懂什么叫铮铮铁骨。
南京的街巷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但纪念馆墙壁上那组浮雕永远刻着真相,数十万亡魂的悲鸣里夹杂着“不能退”的嘶吼。千里之外的滇缅公路上,数十万民工用锄头、箩筐和血肉之躯在悬崖峭壁间劈开了一条生路。
更让人落泪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战场。教授把课本改成抗日教材,在日寇的刺刀下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海的弄堂里,穿旗袍的女学生把抗日传单藏在发髻里,穿过日寇岗哨时腰杆挺得笔直,把信息传递出去;太行山下的村庄里,大娘把仅有的粮食做成炒面,塞进八路军的口袋。他们不是战士,却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当成抗击敌人的战场。
8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上战场,但有些东西得像传家宝一样捧着。还记得以前去社区开展志愿活动,遇到一位90岁的老兵。他给我们看珍藏的军功章,笑道:“那会儿想着,能看到新中国就好了。没想到还能看到孩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读书,比我梦里的日子都好。”
原来,铭记从不是沉重的负担,是我们在教室里朗读“苟利国家生死以”时,能想起那些在狱中舍生取义的志士;是我们对着国旗敬礼时,能懂得那抹红里有杨靖宇将军的血和千千万万无名者的爱国热情。
纪念馆外的老槐树枝繁叶茂,根须在地下盘结,像无数双手紧紧攥着这片土地。风吹过80年,吹黄了家书,吹锈了弹壳,却吹醒了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热爱——爱清晨菜市场的喧嚣,爱深夜书房的灯光,爱这片土地上每个为明天奋斗的身影。
因为我们知道,风里不仅有历史的回响,还有未来的方向。而我们,正是从历史里走来、向着未来走去的人。
此致敬礼!
柴靖坤
2025年8月10日
(柴靖坤,市第二初级中学八(9)班学生,指导老师:陈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