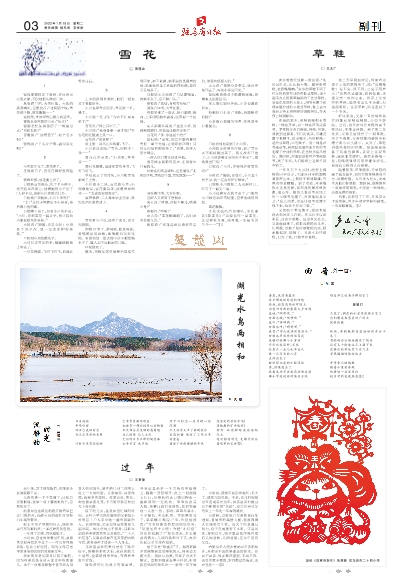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2年01月18日
过 年
□ 王贺锋
大年夜,禁了烟花爆竹,喧闹的小县城寂静下来。马路仿佛一下子宽阔了,比起白天的拥堵,犹如一双卡着喉咙的手,忽然松开了。
街道两边金黄色的路灯映着早已关门的店面,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着小城的繁华。
街上不见了穿梭的行人,偶尔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如沉睡前的呓语。
一年终了的夜,都该歇歇了。
小时候,总是渴望着过年的,意愿其实也再简单不过了——可以穿件新衣服、吃点儿好吃的。因为父母总把平时承诺的兑现时间放到过年。
我家的年是从腊月廿四开始的,因为母亲总是在这天蒸过年吃的馒头。由于一次要蒸够整个春节家人和客人吃的馒头,要在腊月廿三的晚上发上一大盆的面。父亲揉面、母亲做馍,我和弟弟烧锅。红薯豆包、菜包、肉包都要蒸几笼,手巧的母亲还捏出几个枣花馍。
接下的几天,是我家更忙碌的时间。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父亲是小村里百十户人家中唯一能写春联的人。依据经验,父亲记得每家需要几副对联。相比帮母亲干家务,我和年幼的弟弟更喜欢帮父亲裁纸。“二十八贴花花”,父亲必须要在这天前把春联写完,家务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儿时最喜欢的事情是吃了除夕饺子,领着弟弟和大伯、叔叔家的几个堂哥、堂弟挤到爷爷家,等着爷爷发压岁钱。
被昏黄的灯光照着的老屋里,爷爷总是坐在一个黑色的罗圈椅上,戴着一顶旧帽子,点上一根烟吸上几口,从棉袄的大口袋里掏出一叠崭新的一元纸票。爷爷清点完人数,笑着让我们排好队,然后郑重地一人发一张。那时,弟弟年龄小、个子最低,夹在队里。等纸票发完了,弟弟噘着嘴说:“爷,咋没给我发?”爷爷好像忽然发现他似的说:“队里还有个人哩!咋把‘小灯泡’的压岁钱漏了?”现在想来,多么善意的谎言,儿时的我却当了真,再排队便让弟弟排在最前。
接下来是“熬富贵”了。据说在除夕夜能熬到最后睡觉的人,将来会大富大贵。我信以为真,用尽了方法不睡觉。直熬到眼皮支撑不住时,听到街坊邻居的拜年声——新的一年开始了。
小时候,感觉年是那样漫长;长大了,感觉光阴似箭。于是,由儿时渴望过年变成害怕过年,其实是害怕数自己不断增长的“年轮”,更害怕看见父母脸上一年比一年深的皱纹。
小时候,过年坐着父亲的自行车进城,看城里的高楼大厦,很羡慕别人在城里有个家。长大了的我通过努力,终于在城里安了小家。可是现在,每到过年,脑子里总是浮现村里的几棵老树、几间老屋,还有年迈的父母。
看到很多人说乡愁是回不去的故乡,其实回不去的是逝去的时光。你回不回去,故乡都在那里,不离不弃。无论你愿不愿意,岁月都已经流走、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