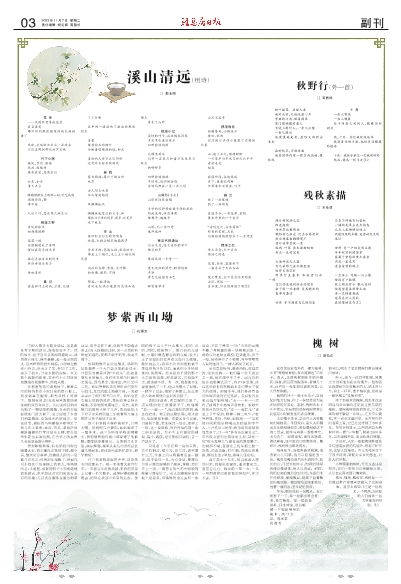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11月07日
梦萦西山坳
□ 孔得方
中国人素来有故乡情结,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故乡,位于遂平县西部的嵖岈山,那里青山绿水、峰峦叠嶂,是一处美丽宜人、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时候总想到山外去,后来上了学,参加了工作,离开了故乡,才知乡愁的滋味。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故乡的小山村悠悠地飘荡在我的梦中,伴我入眠。
在葱葱茏茏的老槐树下,裹着头巾的奶奶坐在小院门前的青石板上,拐杖斜靠在腿旁,阳光从枝丫间洒下。微风吹来,阳光也晃晃悠悠地照在她的深色布衫上。从山里捡回的青石砌了一圈低矮的围墙,多余的石板便摆在门前大树下,这里便成了乡亲们消暑纳凉、吃饭谈天的好地方。初夏时节,墙根的各种藤蔓开始铆足了劲儿往上攀缘:丝瓜、苦瓜、菜葫芦沿着斜插着的竹竿往墙头上爬,野生的牵牛花也来凑热闹,在竹竿上吹奏着几朵淡蓝色的小喇叭。
黄狗眯缝着眼,趴在奶奶的脚边睡着大觉,偶尔懒洋洋地伸下腿、翻个身,继续闭目养神,仿佛这人间的一切都与它无关;母鸡则忙碌极了,领着几只小鸡在草堆里刨土找食儿,咯咯地叫着;小溪里,成群的鸭子不知疲倦地游来游去,似乎游泳对它们来说有无穷的乐趣;几只大白鹅卧在溪边的草丛里,似乎是在下蛋,但我并不敢跑去看,因为大白鹅凶过狗,这一点我和狗都是知道的,狗都不敢干的事,我更不敢干。
悦耳的歌声从远处飘来,邻家的姑姑提着一个大竹篮从坡前走过来,竹篮里装着采回的“牛抵头”,也就是夏枯草的穗儿,有时还有香气扑鼻的金银花,因为是金、银两色,所以又叫二花。姑姑哼着收音机里听来的流行小曲儿,红红的脸上淌着汗珠,一笑起来露出了两行整齐的白牙。姑姑坐在石板上同奶奶说话,黄狗也伸着狗头嗅她,不停地摇晃着尾巴。突然,黄狗朝门前的林子吠了几声,然后就见山下村子来采药的赵三伯挑着两大捆山荆芥从林子里钻了出来。
赵三伯将挑子靠在槐树下,讨碗水喝。奶奶呵斥着黄狗,姑姑端来了一瓢井水。赵三伯咕咚咕咚地喝着水,黄狗嗅着他的被山草染青了的裤腿,慢慢地摇着尾巴。山里的井水甘甜,清凉解渴,城里人来玩的时候总会灌几桶回去,说这是纯正的矿泉水,稀罕着呢!
村口传来拨浪鼓的声音,这是外乡的货郎来了。他一手推着大梁自行车,一手摇着牛皮拨浪鼓,车后的货架上安着一个大箱子。黄狗围着他跳来跳去,仿佛在欢迎山外来的远客。货郎的箱子里几乎什么都有,吃的、玩的、用的,都装得下。爱打扮的大姑娘、小媳妇挑选着喜欢的头绳、发卡;上了年纪的妇女喜欢买些针头线脑,做针线活儿;我和小伙伴则爱他箱子里造型各异的口哨、逼真的小手枪和鱼钩、鱼漂等。尤其是他手里的那个大牛皮拨浪鼓,谁都想买,可他偏不卖,碰也碰不得。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摇了一下,他立马瞪大了双眼,一把夺了过去,掖到了裤腰上,从此便没人敢再摸他的宝贝拨浪鼓了。
货郎还没走,卖豆腐的又来了。卖豆腐的老王推着架子车,吆喝着“豆——腐——”,拖着悠长的腔调,像是在唱戏。老王的豆腐是用山泉水做的,吃起来很水嫩。你要买多少豆腐,只要说个数,老王铜刀一划拉,放秤上一称,这一块准够,然后再给你饶一块二指来厚的。架子车上有调好的辣椒、蒜汁、碗筷,想吃辣椒豆腐的,言一声就行了。
只见老王左手托着一块热豆腐,右手持铜刀,横三刀,竖三刀,再平着片三刀,手掌上的豆腐看着还是一整块,但手轻轻一抖,大小合适、厚薄均匀的豆腐块便落到了碗里,辣椒、蒜汁往上一浇,一碗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辣椒豆腐便好了。有人端着碗坐在石板上吃起来,有嘴馋的也过去捏一块尝尝,不忘了赞美一句:“今天的豆腐不赖。”有捣蛋的挑一块辣椒到地上,黄狗以为是块豆腐渣,赶紧跑来,鼻子一嗅,被呛得打了个喷嚏,哼哼唧唧骂人似的跑开了,一群人都笑了起来。
还有卖凉粉的、灌香油的、收破烂的、收杂皮的……他们隔三岔五就会去一趟,每次都空不了手。因为我的故乡离集镇太远了,有20多里地,所以这些游走的商贩给乡亲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时隔多年,他们各具特色的吆喝声我仍记忆犹新。卖凉粉的大老远就开始吆喝:“大——米——凉粉。”前两个字拖得声音较长。收破烂的则分为好几类:“收——破烂儿!”这是上了年纪的,蹬着一辆三轮车;“收啤酒瓶、废铁、书纸、破鞋底……”这种把回收的物品都喊出来的是些中年人,开着机动三轮车;收杂皮的就喊得简单多了,只一句“谁有杂皮拿来卖”,有些收杂皮的还兼收长头发,就加一句“收头发辫儿”;灌香油的则更懒了,连喊都不喊,直接在三轮车把上挂一块铁,边走边敲,叮叮响,香油也是真香,哪怕走出2里地,香味儿还在呢。
离开故乡十几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坐在窗前,遥望着夜空,遥望着远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屋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中国人素来有故乡情结,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故乡,位于遂平县西部的嵖岈山,那里青山绿水、峰峦叠嶂,是一处美丽宜人、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时候总想到山外去,后来上了学,参加了工作,离开了故乡,才知乡愁的滋味。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故乡的小山村悠悠地飘荡在我的梦中,伴我入眠。
在葱葱茏茏的老槐树下,裹着头巾的奶奶坐在小院门前的青石板上,拐杖斜靠在腿旁,阳光从枝丫间洒下。微风吹来,阳光也晃晃悠悠地照在她的深色布衫上。从山里捡回的青石砌了一圈低矮的围墙,多余的石板便摆在门前大树下,这里便成了乡亲们消暑纳凉、吃饭谈天的好地方。初夏时节,墙根的各种藤蔓开始铆足了劲儿往上攀缘:丝瓜、苦瓜、菜葫芦沿着斜插着的竹竿往墙头上爬,野生的牵牛花也来凑热闹,在竹竿上吹奏着几朵淡蓝色的小喇叭。
黄狗眯缝着眼,趴在奶奶的脚边睡着大觉,偶尔懒洋洋地伸下腿、翻个身,继续闭目养神,仿佛这人间的一切都与它无关;母鸡则忙碌极了,领着几只小鸡在草堆里刨土找食儿,咯咯地叫着;小溪里,成群的鸭子不知疲倦地游来游去,似乎游泳对它们来说有无穷的乐趣;几只大白鹅卧在溪边的草丛里,似乎是在下蛋,但我并不敢跑去看,因为大白鹅凶过狗,这一点我和狗都是知道的,狗都不敢干的事,我更不敢干。
悦耳的歌声从远处飘来,邻家的姑姑提着一个大竹篮从坡前走过来,竹篮里装着采回的“牛抵头”,也就是夏枯草的穗儿,有时还有香气扑鼻的金银花,因为是金、银两色,所以又叫二花。姑姑哼着收音机里听来的流行小曲儿,红红的脸上淌着汗珠,一笑起来露出了两行整齐的白牙。姑姑坐在石板上同奶奶说话,黄狗也伸着狗头嗅她,不停地摇晃着尾巴。突然,黄狗朝门前的林子吠了几声,然后就见山下村子来采药的赵三伯挑着两大捆山荆芥从林子里钻了出来。
赵三伯将挑子靠在槐树下,讨碗水喝。奶奶呵斥着黄狗,姑姑端来了一瓢井水。赵三伯咕咚咕咚地喝着水,黄狗嗅着他的被山草染青了的裤腿,慢慢地摇着尾巴。山里的井水甘甜,清凉解渴,城里人来玩的时候总会灌几桶回去,说这是纯正的矿泉水,稀罕着呢!
村口传来拨浪鼓的声音,这是外乡的货郎来了。他一手推着大梁自行车,一手摇着牛皮拨浪鼓,车后的货架上安着一个大箱子。黄狗围着他跳来跳去,仿佛在欢迎山外来的远客。货郎的箱子里几乎什么都有,吃的、玩的、用的,都装得下。爱打扮的大姑娘、小媳妇挑选着喜欢的头绳、发卡;上了年纪的妇女喜欢买些针头线脑,做针线活儿;我和小伙伴则爱他箱子里造型各异的口哨、逼真的小手枪和鱼钩、鱼漂等。尤其是他手里的那个大牛皮拨浪鼓,谁都想买,可他偏不卖,碰也碰不得。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摇了一下,他立马瞪大了双眼,一把夺了过去,掖到了裤腰上,从此便没人敢再摸他的宝贝拨浪鼓了。
货郎还没走,卖豆腐的又来了。卖豆腐的老王推着架子车,吆喝着“豆——腐——”,拖着悠长的腔调,像是在唱戏。老王的豆腐是用山泉水做的,吃起来很水嫩。你要买多少豆腐,只要说个数,老王铜刀一划拉,放秤上一称,这一块准够,然后再给你饶一块二指来厚的。架子车上有调好的辣椒、蒜汁、碗筷,想吃辣椒豆腐的,言一声就行了。
只见老王左手托着一块热豆腐,右手持铜刀,横三刀,竖三刀,再平着片三刀,手掌上的豆腐看着还是一整块,但手轻轻一抖,大小合适、厚薄均匀的豆腐块便落到了碗里,辣椒、蒜汁往上一浇,一碗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辣椒豆腐便好了。有人端着碗坐在石板上吃起来,有嘴馋的也过去捏一块尝尝,不忘了赞美一句:“今天的豆腐不赖。”有捣蛋的挑一块辣椒到地上,黄狗以为是块豆腐渣,赶紧跑来,鼻子一嗅,被呛得打了个喷嚏,哼哼唧唧骂人似的跑开了,一群人都笑了起来。
还有卖凉粉的、灌香油的、收破烂的、收杂皮的……他们隔三岔五就会去一趟,每次都空不了手。因为我的故乡离集镇太远了,有20多里地,所以这些游走的商贩给乡亲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时隔多年,他们各具特色的吆喝声我仍记忆犹新。卖凉粉的大老远就开始吆喝:“大——米——凉粉。”前两个字拖得声音较长。收破烂的则分为好几类:“收——破烂儿!”这是上了年纪的,蹬着一辆三轮车;“收啤酒瓶、废铁、书纸、破鞋底……”这种把回收的物品都喊出来的是些中年人,开着机动三轮车;收杂皮的就喊得简单多了,只一句“谁有杂皮拿来卖”,有些收杂皮的还兼收长头发,就加一句“收头发辫儿”;灌香油的则更懒了,连喊都不喊,直接在三轮车把上挂一块铁,边走边敲,叮叮响,香油也是真香,哪怕走出2里地,香味儿还在呢。
离开故乡十几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坐在窗前,遥望着夜空,遥望着远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屋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